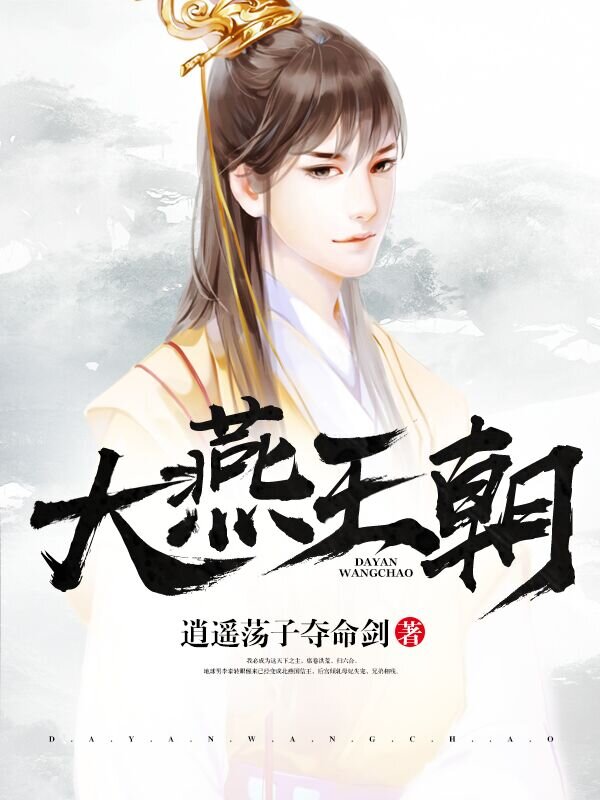
-
大燕王朝
第十四章秉烛夜谈(下)
皇弟,你也说说朕立太子之事,你认为谁可继承太子之位。朕的二子李贞祐才思敏捷,温润典雅、德才兼备。善结交文人雅士,喜论赋做诗。在朝堂之中有雅名,人人称贤,有仁德之心、宅心仁厚,皆言可堪大任。朕的三子李慎有胆略,武艺超群,在军中也有威望,军功甚伟。粗射文略,笃厚恭谨。六子李简,高风亮节,兄友弟恭。从小让太傅称之神童,现仅十三,论才智,朕也比不过他!我在这三人之中徘徊,为之奈何!"李希烈看时机已到,再次开口道。
这让李文忠身体一颤,双手颤抖,嘴唇微动。酒杯摔在地上,却许久没有开口。
"皇弟,你意下如何?"李希烈的语气急了。
"陛下,臣不能言。臣离京已有十年,京中之事一概不知。就如刚刚承乾之事,陛下未说,臣怎么能知。当时离京,陛下诸子接年幼,承乾已是陛下中意人选。可是承乾死了,臣不知如何说!"李文忠被逼无奈,缓缓开口。
"祐儿?慎儿?还是简儿?皇弟,你意下如何?"李希烈似乎在询问李文忠,似乎又在喃喃自语。
"陛下!皇兄……"
李文忠突然半跪在李希烈面前,面容凄苦、悲伤,一副犹如赴死之相。
"皇弟,这是干什么!快快起来,这都是朕的错,不应该牵涉皇弟。"李希烈不顾天子礼仪,慌忙地将李文忠扶起,但跪地之人如同泰山,怡然不动。任由李希烈怎么推拉,都不肯起身。
"皇弟……"
"陛下今日问臣弟,臣与陛下感同身受,此那关乎大燕万世江山,千古社稷,不得不慎重!但他日陛下还会问臣,后日还会问臣,再日还可能问臣。臣又该如何回答,臣真的不知。臣只知道忠君爱国,恪守君臣之道,抵御敌寇而已。陛下选谁做日后太子,甚至是日后天子。臣必遵旨,就算是下刀山赴黄泉,后世留下千古骂名。臣弟也无怨无悔!"李文忠边磕头边言,眼眶泪水夺目而出。
"皇弟今日之言,朕茅塞顿开,永世难忘。快起来,这件事朕日后不会再问,听弟之言,朕心中已经有答案。文忠,你永远都是我的右臂,镇南王之位将会世袭,今日我在此发誓,永不削南番。"李希烈长吁一声,将唯一能托付的人扶起。
"臣弟叩谢皇恩,皇恩浩荡,永世不忘。"李文忠郑重的叩首。他知道这是天恩,更是皇帝的托付,皇上这是为后面之事做准备,未雨绸缪。
"是朕最近心太乱,这件事就翻过去。皇弟,弟妹身体可好。她从小就体弱多疾。如今你们在南方,水土不服。母亲可是很挂念她,但每年都缺席,这一点我每次去母亲寝宫都让她叨扰。"李希烈话锋一转,将话题转到家事。关切问道。
"臣妻诗禧自幼多病,一到冬天,就手脚酸痛,行动不便,但没有大碍。这上京路途遥远,山多歧路。臣弟怕她受不了颠婆之苦,所以一直没有带她来。六年前,陛下可记得臣弟发来的喜帖,诗禧又为臣诞下一子。现在已经六岁,今年她自然就没有来了。"李文忠愁苦的脸终于出现笑容,面带春风。
"看过,可喜可贺之事。皇弟宝刀未老,为皇家开枝散叶。朕甚欣慰,你有二子一女,我亦有九子四女,没有让我皇家绝嗣。还记得六皇叔吗?"李希烈笑吟吟的说道。暗想,喜帖之事,当时不过匆匆看过一眼。早已经忘记,帖子不知道丢到那里去了,后面连礼物都没有送过。文忠对他可是情比金坚,但他如此,他这个皇兄不称职啊!
现在文忠回京,他要弥补亏欠,一报兄弟之情。
"当然记得敦皇叔,李富敦。他当年可是教过我武艺,我当初受到他很多关照。过几日,我就想去拜访他。"李文忠不禁陷入回忆,沉思道。
"他的独儿在游湖之时,不幸溺死。而他的孙子也不幸早夭。整个辛王府空空荡荡的,甚是凄凉。过几日,我陪你一起去。我也好久没有看他了,秀儿也在那里。"
"怎么会这样,连溪弟也去世了。看来我离开这里确实太久,久得臣已经连故人离去,都一概不知。秀儿,不是陛下之子吗?"
"当年敦皇叔帮朕很多,朕怎么忍心让他一个人孤独终老。就将朕的小儿子过继给敦皇叔,当他的孙子。不让他绝后,他也是先皇一辈唯一在世的男性皇族了,我要好好待他。你也在这京城多留一段时间,我们好好聚聚。"
两人发出噫吁,叹息之声不停,随即桌上之酒让两人痛饮,准备今日不醉不归。
时光荏苒,岁月如白驹过隙。当年之事,就犹如黄河之水,滚滚东逝!
"对了,文忠。你的女儿哪,朕在宴会上怎么没有看到她,她可是要做朕的儿媳。"李希烈想到儿女婚姻之事,不禁来了兴趣。
"这……小女天性顽劣,刁蛮任性。在到京城的路上乔装打扮逃了,不知所踪。臣弟才耽搁片刻,派人寻找。我看多半是在京城之中游玩。陛下也知道她长得和诗禧一模一样,身体却很健康,我自然视为珍宝,谁知道她如此不听话!我找到她,定捆着她来见陛下。"李文忠面带不忿,但语气中的透露出的父爱却表露无遗。
"没事没事,朕也为我的泰儿心烦。年轻人就是这样,当然我们还更大胆,不也是现在这样。"李希烈先是捧腹而笑,后随意的摆了摆手,表示他不放在心上。
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弟弟,居然在女儿手里吃瘪。看看他,儿子李泰让收拾的服服帖帖。这感觉不错!
"李泰发生何事,惹陛下生气。我听说李泰不过回京二个月。"
"和皇后在永春宫吵架,甚至持剑威胁皇后,原因不过一琐事。我就把他禁足三个月。"李希烈谈谈的说道。
"陛下,永春宫,不是柔皇嫂的寝宫吗?杨丽华就算是皇后,也不能如此目中无人。"李文忠对杨丽华直呼名讳,毫不客气。
原因?当年李文忠离京,一半的破事都是杨丽华挑拨唆使,李文忠不想破坏李希烈与诸妃的关系,让大臣谏言,说皇室不和。只能带着妻子离京,去了南方,留得耳根清净。
"后宫之事复杂,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现在丽华已经是大燕皇后,你见到,切忌不可再直呼其名,实在不行就叫皇嫂。当年之事,就如同这酒,没了吧。"李希烈将杯中满酒呈到李文忠面前,面带诚恳。
李文忠豪爽的喝光了酒,顿时感觉头昏脑涨,身体摇摇欲坠。酒壮怂人胆!心中积攒多年怨气无处发泄,现在犹如火山爆发一般,喷涌暴发。
"陛下这样说,臣弟自然照办。只不过我想不通皇后之位为什么要给她,当年甄姐姐命薄,不过三年就离开我们。陛下也一直没有立正妃,陈善柔皇嫂温柔贤淑,可以说是正妃的首选,皇后之位自然可以胜任。实在不行,还有周圣洁、刘妙君两位皇嫂可以选择,这两个人都比杨丽华好多了。想当年,杨家暗中使绊子还少吗?"
"杨家可以说是大燕的名门望族,四世三公,门生故吏遍天下。先皇之时,杨家有三人就在朝中当尚书,可谓位高权重。当时我们出兵时他们也算的出了力,没有他们,我们也不会那么顺利进京!十年前,陈家让杨家告谋反,证据确凿,朕有什么办法。如今朝堂之上,杨家一族独霸,如日中天。朕这个皇帝也要忌惮三分。更有周家、刘家、王家虎视眈眈,让朕如坐针毡!"
"皇后,你以为是朕愿意册封给她的吗?是杨家暗中出头,窜拨朝中大臣联名上书请求立后,朕势单力孤,加上三宫多年无主。只能勉强同意!"李希烈眼露精光,远看犹如虎狼之目,让人不寒而栗。
他何尝不想铲除杨家这个毒瘤,区区世家居然想和皇族分权抗衡,妄图平分天下。这是李希烈作为一位英主,忍受不了的。但缺少一个理由,一个光明正大,让天下士人闭嘴,还会称赞皇族判事公正的理由。




